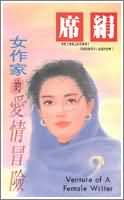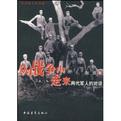对话著名作家-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辛吮浠拿缤罚倭说雌鸱那榻冢宋锝粽诺那樾饕彩婊毫耍适滦浴⑿钚砸裁挥幸酝苛伊恕U馐遣皇怯捎谀陨娴睦斫庥兴谋淠兀俊!∽詈玫膖xt下载网
刁斗(9)
刁:如果说我的写作出现了变化,也许它更出于一种摆脱惯性勘探新途的美学需要,是风格的与形式的需要。这就好比某样东西好吃,我也认可它好吃,可总吃它也要倒胃口的。但必须承认,技术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在潜移默化中,思想意识上的东西的变化才起决定作用,尽管,它是一股暗流我都不很自知,甚至它完全就由一些客观原因促成。举个例子,我今年发表的《哥俩好》受到不少朋友好评,而好几个人都特别提及它结尾处理得好。这就不能不让我拍拍脑门了。其实原稿的结尾,那个弟弟自杀了,从哥哥摔下楼去的那个窗口跳了下去。可程绍武和李敬泽都觉得那么处理太激烈了,尤其是程绍武的来信,很让我震惊,他认为我让弟弟自杀有偷懒之嫌。对我来讲,在小说上“偷懒”正是在创作上自杀。当时虽然我仍有保留,但尊重了他们的意见,加一千字,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看来,我喜欢上了改过的结尾,屈服于生活确实比逃避生活更有力量。在此我顺便向程绍武李敬泽这两位高质量的编辑表达谢意。
也就是说,我对生存的理解是始终没变的,但在如何看待我的理解和把握我的理解上,我有了超越,我比原来的自己大了一点,高了一点。我说的是心胸和眼界。
张:我在网上看见了这样一则消息,说今年6月在贵州凯里的一次笔会中,您说了这样一段话:“文学有承担,那么数学有没有承担?烹饪学有没有承担?厨师可能还有一种具体的承担;文学只承担一种内心的东西。文学可以对社会的承担很弱小,只需对自己负责任。”其实,类似的想法很多其他作家也表露过。那么,您认为作家们对文学“承担”的抵触,是对曾经的满载“承担”的文学的厌恶,还是由于文学的边缘化,作家已不被赋予使命,不能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无奈?
刁:这是个含有伪命题成分的话题,更是个容易被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话题。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承担的东西怎么能没有呢?我想作家不是抵触社会担当,而是抵触那种强加于人的假大空的东西,抵触那些不属于小说的非艺术的东西,这跟小说边不边缘也没关系。在人类社会中,处于中心地带的永远是政治和经济,它们在利益好处上能立竿见影;而某种意义上,艺术的事情与功利无关,边缘是小说最合适的位置。如果一种力量把小说这个东西带入了社会的中心地带,那这种力量肯定是恶的力量,是在*小说。中国是个政治大国,现在经济似乎挤进中心了,但仍然是个暧昧的角色,陪绑的角色,它名分的得到非常勉强,极其实用,还远远名不副实。我敢打赌,如果哪个作家对他的边缘身份牢骚满腹,那你给他个官当,比他现在的官大一级半就行,交换条件是放弃写作,他准干。
张:在这次会上,马原又重申了他的“小说已经进入它漫长的死亡期”的观点,之前文坛上也一直有关于“小说死了?!”的争论,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刁:我认为文字不死小说就有生命力。当文字只用于书写合同书或广告词,而放弃了它的文学功能时,文字的死期就来到了;可如果人类还存在,并且在吃饱肚子之外还有别的欲求,比如表达和倾听,比如提炼和抽象,那它就离不开文学。文字能够分泌文学,文学又反过来滋养文字,这是文字的历史,而文字史,它是人性史的一条辅助线。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高级,就在于他除了需要实在世界,也需要虚有世界,而驮起虚有世界的一对翅膀,就是宗教和文学。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多年前还特别无神论唯物论,可近些年,我对宗教的精神充满敬意,我知道它不是轻易就能被世俗化的;而对语言文字的使用,通过语言文字,以文学的方式去关注问题,考量人性,探究世界,它同样是任何高科技数字化与影视图像都无法替代的。当然我只是一个个体的我,但我相信吾道不孤,相信不会有人不渴望出入虚有的天地,尽管,那出入的方式可以各有不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刁斗(10)
但预言小说死活之事,不论多么悲壮或多么隆重,四十年前的巴斯也好今天的马原也罢,我都愿意把他们的危言耸听放在搞笑的层面来赏玩。想想球王贝利吧,他对历届世界杯的胜负预测,不都成了像世界杯本身一样让人解颐的乐子吗?
张:在您的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外国作家的人名和外国作品里的人名(尤其集中体现在《证词》中)。像福楼拜、霍桑、卡夫卡、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索尔?贝娄、米兰?昆德拉等名字在您的作品和创作谈中举不胜举。显然您受外国文学影响很大,好像还尤为推崇法国新小说。那么外国文学都给了您哪些重要启示?另外,您有喜欢的中国作家吗?
刁:马原就是我喜欢的中国作家呀。随着阅读的不同和心境的不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接受对象,但总体上对某种风格某种特点是有偏爱的。十多年里,我书房挂的唯一一幅照片,始终是贝克特与新小说的格里耶、西蒙、萨洛特那几个人的合影,我对那些形式主义者的好感达到了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我比较喜欢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小说,一方面,它们的叙述调子与构成方式符合我的美学趣味,给我带来的愉悦感更强;另一方面,它们对于普遍人性和日常生活的关注角度与关注立场更让我认同,更贴合我的参悟与感受。有人认为我以及与我类似的小说家把西方文学作为营养是喝狼奶,是对中国祖宗的大不敬。我觉得这样的言论既狭隘自卑,又文不对题。打个比方说,如果我爸的能力只够教我到高中,大学之后我另拜师傅,就不对吗?如果我爸只能教我数理化,我在文史哲上另投他门,就不行吗?再往极端处说,如果我爸吃喝嫖赌,不学无术,我不敬他责任在我吗?人类文明的薪继火传,没人规定只能继中国的薪,传汉族的火,小说在中国是叙事的艺术,在英法德俄西葡日,也并未变成社论檄文表扬稿呀。人性中那些基本的东西是共同的,区别只在于他为级别喜或者悲,你为收入喜或者悲,我为恋爱喜或者悲。
张:您能谈一谈近来的创作情况吗?有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吗?
刁:平常没什么杂事干扰我,我每天的乐趣就在于看书写作和玩,我觉得我伏案的时间比大部分同行都长。但写作这东西,其实越写越心虚,或者叫要求越来越严格,越往前走越愿意自行设置障碍,让自己和自己掰掰手腕,所以我产量没过去高了。我总在否定自己,不断修改写完的东西,经常枪毙成熟的构思甚至成稿。也正因为这样,去年就开了头的一个长篇,一年多了还只有两万多字放在那里,倒是没事就看看改改,却不敢往下写,觉得它在它的虚有世界里还没熟透,我还不该去采摘它。这两年写了几个中篇,除了发在《人民文学》上的《哥俩好》,还有《的》、《身份》、《出处》和《虐恋考》,分别发在《当代作家评论》、《花城》、《山花》和《小说界》上,现在拟发的有《狗肉豆腐汤》与《三界内》,尚未出手但已基本定稿的有《梅杜萨之筏》。
毕飞宇(1)
毕飞宇简介
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
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南京特教师范学校教师、《南京日报》社记者。
1995年,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里说话》获《人民文学》奖。
1996年,《哺乳期的女人》获《小说选刊》奖、全国十佳短篇小说奖、1995—1996《小说月报》奖、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2004年,《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
现供职于《雨花》杂志社。
毕飞宇自述:对命运与性格的好奇
毕飞宇
我喜欢许多东西,其中有一样叫关系,也就是男女关系的关系。我们活在世界上,自然和这个世界就有了关系。这个关系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感受和判断中。因为是“我们”的感受和判断,这一来就有意思了。人和人不一样,有些人是一块平整的玻璃,透过他,你看到了什么世界就是什么;有些人是凸透镜,从他的身上你只能看到放大的本体,真相永远是巍峨的,阔大的;有些人是凹透镜,所有的一切到了他那儿就缩小了,千丝万缕,纤毫毕现;而有些人干脆就是镜子,他是阻隔,你从镜子里只能看见他自己,当然,还有一些被颠倒的东西。所以,可供所有人信赖的关系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一个人构成了一种关系。
关系这东西就是这样变得可爱起来的。它有了蛊惑人心的魔力。究竟哪一种关系是可靠的,真实的?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是,有一种人,他渴望知道,这个人就是作家。作家最渴望得到的是一个数据,那就是,你的感受与判断和这个世界能不能够成1∶1的关系。换句话说,你能真正地知道世界的真相吗?你凭什么就认准了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呢?
由此,人与人成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它是写作的困境,也是“活着”的困境。
更可怕的一点还在于,这个世界上有极权,极权给我们下了死命令,它告诉我们:“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认为世界不是“这样”,你就必须受到“教育”与“改造”,在“教育”与“改造”过后,我们变成了一个浩大的集体,中国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集体。我们在集体之中,我们为集体而活着。
在许多时候,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其实处在泰坦尼克号上。当泰坦尼克要下沉的时候,你只能往下沉。这就是我反反复复在写的东西。我与这个世界究竟可以构成怎样的关系?这是推动我进一步往下写作的基本力量。二
我的小说,写了很多种类型的人物。但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的,一是农民,一是女性。《玉米》、《青衣》,包括我的新书《平原》都是这样。
“五四”之后,面对中国的农民,许多作家都做了很多很好的功课。但是我认为,除了鲁迅以外,大多数都做得并不好。我说做得不好,依据是什么?我的依据是,许多作家都有一个道德癖,在他作为一个精英分子出现的时候,他是带着感情来的,来干什么?来发放同情。我们的文学似乎有了这样的一个铁律:把同情心给了农民,然后,像模像样地洒一两滴泪,他的工作就完成了,同时,他自我美化的壮举也就完成了。鲁迅不这样。鲁迅面对农民的时候,他会仔细地看,正过来看,反过来看,甚至,翻过去看。鲁迅的“农民”立体感要强得多。就凭这一点,鲁迅高出了同代作家一大截。其实,在农民这个话题面前,作家是很难下手的。举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到南京师范大学跟同学见面。一个同学到我家去接我,接我的时候路过楼的拐角,几个农民正蹲在那儿。那个同学自言自语说:“纯朴的农民。”我立即就停了下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是纯朴的?你的依据是什么?我告诉他,“纯朴的农民”是一个判断,你这个判断是你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作为一种知识给你的,而不是生活给你的,不是你和农民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构成了丰富、复杂的人际关系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你要说纯朴的农民,我希望你把你老师的话全部忘掉,等你和农民有了接触,和农民一起生活、血肉交融的时候,那时,你说纯朴的农民,我就信。我要说的是,农民身上有纯朴的一面,有绝对善良的一面,但是千万别忘了,农民身上还有极其残忍的一面。但是,对于农民身上的残忍,轻易地去批判,我恰恰又是不敢的。为什么?农民的残忍自有其原因,一旦他失去了残忍,他也许就无法活下去。所以,我首先要关心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我们的农民不需要残忍,他还可以体面地活下去!所以,关于农民,这几年我在反反复复地写,其实,每一次写的时候,我都特别犹疑,特别困惑。《平原》里写的也是农民,但我不敢说,我对农民有了发言权。对我来说,农民问题依然是个巨大的黑洞。
毕飞宇(2)
我的小说另外一个人物类型是女性形象。玉米三姐妹,《平原》里的三丫、吴蔓玲,都是我比较用心的对象。谈到这里,我可以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只有妇女解放了,社会才会解放。”我想,如果我这样说,很可能体面一点。但是,我不想说谎,我写妇女,动机不在这里。我的动机还是对命运和性格的好奇。在命运和性格面前,写男人和写女人是一样的。有人以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不是。女权主义能否成为人文主义之外的一个主义,我是怀疑的。我每一次出门参加活动,都会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总盯着女人不放?我的回答其实也是一样的,相对于文学来说,人物是无性别的。我没写女人,我写的是人。当然喽,在写作中,我不能犯常识性的错误。比方说玉米若是男人,我不会安排她去生孩子,比方说筱燕秋若是男人,我不会安排她去堕胎。但除此以外,人生中的一些境遇,人内心对疼痛的敏感,人对外部世界的体验,我觉得是一样的。如果作家关注的问题,仅仅是女性的问题而男性可以逃脱,反过来说,如果仅仅是男性的问题而女性可以逃脱,那么我觉得这个作品可以不写。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有很多优秀的作家,譬如一出道就达到了极高水准的苏童,他极有天分;譬如后天完成得特别好的王安忆。你问我最热爱谁?莫言。莫言是伟大的小说家。我喜欢他身体好。他身体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我认准了他身体好。当我作为一个读者去看小说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