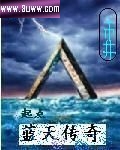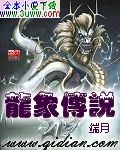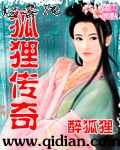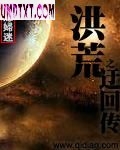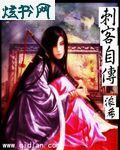李济传-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个口号表明史语并举的主张。他出版的著作《性命古训辨证》,便使用了由语言学入手进而讨论思想史诸问题的方法。第二个口号,傅斯年解释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史学的革命才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变革。第三个口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显示了与列强抗争,为中华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傅斯年在给陈垣的一封信中,曾表示对西洋学术羡妒交加的情绪,既肯定他们在东方学研究上的成就,“并汉地之历史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同时又“惭中土之摇落”,希望能建立一个机构,聚合一群学者奋起直追傅斯年致陈垣函,转引自王汎森:《王国维与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一文。。李济曾以相同的情绪分析当年的情势与傅斯年的心态:地质调查所倡导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协和医学校进行的体质人类学,以及以北平为活动中心的外国学术团体所遣送的各种科学工作远征队,皆是坚强的组织;气势极盛,愈来愈猛。主持这些事业的,除地质调查所外,都是外国的科学团体。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资料也引起了他们的绝大的兴趣。他们很坚决地跑到中国来,调查我们的语言、测量我们的身体、发掘我们的地下古物、研究我们的一切风俗习惯——这些“学问原料”真是一天一天的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
这些野心勃勃的西洋科学家,万里长征跑到中国来工作,不是专凭着他们的政治优势来的;他们更有一套学术上的理由说给中国人听,使听的人亦可感觉到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乱哄哄的中国能够拒绝这些学问上的访问么?残余的北洋军阀政府认识这些工作的意义么?并且他们所注意的资料,大半都是我们自己所忽视的。无论照什么标准说,我们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反对别人来检取我们自己所毁弃的资料。
要反对这种文化侵略,应该先从反对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应该先教育自己认识自己的历史,懂得自己的语言。这些大道理,是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学术界所深知的;却是直等到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有组织的表现。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李济文集》(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64—165页。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4)
1931年史语所与北平研究院部分同人摄于北平静心斋,右起:一排李济、吴稚晖、黄文弼、裴文中、徐中舒;二排赵元任、傅斯年、董作宾、□□□、丁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傅斯年在找寻,在聚合一批同志;也在等待一位能够与他抬杠、吵架而最终不弃不离的诤友。
第三节济之找寻彦堂首掘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最后两年,李济开设的考古学人类学几乎被视为“屠龙之技”。西阴村发掘的成功刺激了他,他在寻思能不能有更大的发现,也在找寻一个理想的合作团队。1927年底,李济赴陕西作考古调查,受北伐战事影响,平汉铁路多处中断,只能从天津坐海船绕道大连、南京、上海,转溯长江去汉口,再走西北。首途大连,李济顺路拜访了退隐后的丁文江。他写道:那时他的太太有病;济瀛丁文江夫人史久元的侄女,后嫁给丁文江的胞弟丁文治。尚没结婚,与他们同住作伴。我进门时正看见她替姑父画地质图。与在君谈了数小时,我没有感觉到他做了一任大官的味道,也没有感觉到他有任何失意的气象。他仍是我在天津与他初见面的那个样子;想法子帮我完成旅行调查的计划;替我写了好些介绍信。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文集》(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77页。船过南京,李济手持丁文江的介绍信去了新成立的大学院。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与他谈得很投机,对他的田野调查也非常支持。李济有一个想法,想尽快摸清中国地下文物和遗址的家底。为此,他邀请了清华的同事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入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同行,相约在开封会合。
梁思永的身份是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的研究生,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国实习。梁启超对儿子耳提面命,他在1926年12月10日写给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西阴村发掘,他说:“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1927年初,梁启超出席清华欢迎李济、袁复礼归来茶话会的当晚,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又说:“(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还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两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思永于是提前回国在清华担任助教,整理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出土的陶片,并以此准备毕业论文。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论文资料毕竟不是出于自己参与的田野发掘,他希望与李济一同外出,找到一处可供实践的发掘地。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5)
转眼就是1928年初,李济在开封焦急地等候迟迟未到的梁思永。1月26日,李济写信给上海的胡适,请他将另附的一封信面交梁思永。李济在给梁的信中谈到,在汉口得知,襄河一带旅行“极危险”,来往商人需化装,且不能携带行李。本打算经鄂西去陕西的李济曾于1924年在鄂西做过体质人类学调查。,“据说:秦岭一带也是一个土匪窝。所以由长安入汉中现在不能做到。”信中没有明说此行的最后目的地,想必是形势复杂,许多因素难以估计。信中谈及有一个机会,冯玉祥打算派人从开封西去敦煌、南到叙州去照相,以作他的《十七年来国民军的纪念》一书的插图。照相的人有军队保护,李济因此有意“随这队人往甘肃走走”。从他托梁思永在上海代购“照壁画用”的照相器材推想,他当时还考虑去敦煌一带。信中还为梁思永的西行路费设想了几种方案,其中之一是已致信李仲揆(四光)“请他替我筹两佰圆与你”。不知什么原因,梁思永根本没去上海,当然也就没能见到这封信,未能与李济结伴而行。李济的调查计划也就半途而废。
留学美国时的梁思永。(梁柏有提供)
1928年8月,梁思永返美,继续完成哈佛的学业,他依据对李济西阴村发掘物研究完成的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HisYin Tsun,Shansi,China。,于1930年正式出版。他也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甫一成立,当务之急是“新其工具,益其观念”,“扩张研究的材料”,重建古史。傅斯年看来,寻找史前和中国历史时期的连接,也许安阳发掘是最好的选择。他认为:“就殷墟论,吾等已确知其年代,同时并知其地铜器石器兼出。年来国内发掘古代地方,每不能确定时代,如安特生、李济诸君所作,虽生绝大之学术问题,而标年之基本工作,仍不免于猜度。如将此年代确知之墟中所出器物,为之审定,则其他陶片杂器,可以比较而得其先后,是殷墟知识不啻为其他古墟知识作度量也。”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7页。于是1928年8月,他派史语所编辑员董作宾董作宾(1895—1963),河南南阳人。自学,后北大旁听生,1924年,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攻民俗学。毕业后曾在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入中研院史语所。前往安阳小屯调查殷墟情况。
董作宾赶到安阳,他找到在开封上学时的老友、河南省立十一中校长张天骥,说明此行目的。张告诉董作宾,三年前,他曾带学生到小屯做过调查,村北洹河岸边的农田里有字骨片已很少见,如掘地一尺,还可见到很多无字甲骨碎片。董作宾在好友徐静轩的陪同下去到小屯村,花十个铜元雇一女童当向导,找到村东北洹水西岸的一个沙丘,果然看到一个连着一个新挖的土坑。他亲眼看到很多新出土的甲骨后,立即断定此地并非罗振玉所说的“宝藏已空”,而是“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他写信呼吁中研院,“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6)
中研院总办事处赞同董作宾的报告,授命史语所负责殷墟发掘。董作宾代表中研院来到开封与河南省政府交涉,河南派出张锡晋、郭宝钧等人参与其事。他们共同制定了周密的发掘计划,然后去到安阳,驻扎在小屯村附近的洹上村彰德高级中学。此次发掘机构的名称是“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员会”,中研院拨款一千元作为发掘经费,委托董作宾全权负责。
在10月13日的晨光中,一群民工挥动了镢头,工地划为三个区,一区在村东北洹水边沙丘上,二区在村北地,三区在小屯村中部。依据“轮廓求法”开展发掘,人员分为四组。所谓“轮廓求法”,即假定某地为甲骨集中地,先在“周围打四坑以探求其轮廓”,然后再向中心挖掘。工作并不如意,一天下来,除了一堆堆的黄沙土,几乎没有什么发现。第二天,董作宾改用“集中求法”,即集中力量在地面多甲骨处挖掘,以图一次挖尽,共开挖六个探沟,仍无所获。
有人告诉董作宾,春天,北伐军在洹水上与当地军阀作战,贻误了农时,小屯的农民只得靠董作宾在书写甲骨文。(董敏提供)
挖甲骨卖钱维生。有些地方被轮番挖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发现,而村前韩姓宅院南侧大路旁,出过大批龟骨,但是只挖了几尺深。董作宾立即前往打探,果然发现了一些重要迹象。他调集所有力量在这一地点,亲自督战,收效依然甚微。他向傅斯年报告:“观以上情形,弟甚觉现在工作之无谓,不但每日获得之失望,使精神大受打击,且劳民伤财,亦大不值得。……试想发掘已三十六坑,而得甲骨文字者,不过六七处,且有仅此三数片者,有为发掘数四之残坑者,有把握者不及全工五分之一,岂敢大胆做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所档”。此处为“所档”:元字第23号。
傅斯年眼光高远,自然不会为董作宾的情绪左右,他在回信中开导说:“连得两书一电,快愉无极,我们研究所弄到现在,只有我兄此一成绩……得一骨骼、得一骨场,此实宝贝,若所得一径尺有字大龟,乃未必是新知识也。此兄已可自解矣。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盖文字固极可贵,然文字未必包新知识。”所档:元字第23号。傅斯年后来评论这次发掘,“董君试掘十余日,知其地甲骨文字之储藏大体已为私掘者所尽,所余多属四下冲积之片,然人骨兽骨陶片杂器出土甚多。如以中国历来玩骨董者之眼光论之,已不复可以收拾。然以近代考古学之观点论之,实尚为富于知识之地。”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7页。
董作宾修习国学出身,优势在于文字,并不懂得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田野发掘非其所长。因此,傅斯年把殷墟发掘的希望寄予新人。
第四节出掌考古组帅印
1928年3月12日,毕士博致函李济:“前函已转知Mr。 Lodge请您尽快来华盛顿之意。他建议您带西阴村研究材料来。”所档:考21—2—2。这实际上是毕士博安排的一次述职活动。秋天,李济赴美成行,他到华盛顿与弗利尔艺术馆洛奇(Lodge)馆长商谈继续合作事宜。经过近距离的接触,洛奇对李济的能力有了进一步认知,决定继续赋予李济全权处理与中国学术机关合作进行考古事宜。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7)
李济返国时绕道欧洲,经香港,10月到广州,顺便到中山大学访友,与傅斯年不期而遇。此前,蔡元培、杨杏佛、李四光等人都分别向傅斯年推荐过李济。傅在写给清华的旧雨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位的信中,已出现了“李仲揆(即李四光)盛称李济之”的字样。傅在这封信中谈到李济,“……我见其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此事我们两面如何合作,乞示知!”
李济在旅美途中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