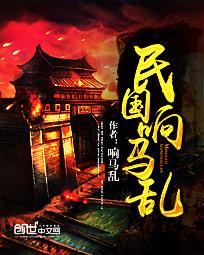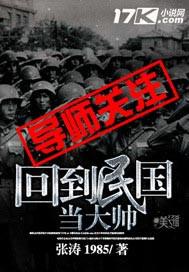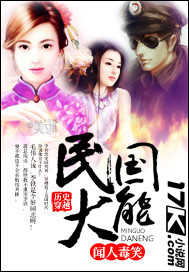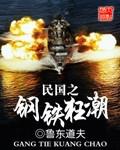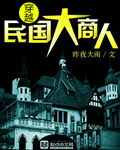�������-��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ķ�ѧҵ������������������̻��ձ���һ��3�ꡣ��ͳ���ư�������˻����ijDZ����������찲���ɡ�ĸ�����ҵ�һ��������Ե��úù�������������������֪���ġ����Ӵˣ����˷ֱ����������ķ�Ĺ��һ������ͷ��һ������ͷ��ֻ�л�ԭ�����꣬���˶����������Ŀ�ɬ��
����1909��8�£�³Ѹ�ع���1910��7�£������ˣ���������ʦ��ѧУУ�������������ˣ�³Ѹȴ�Թ������Ϊ�ɣ��ؼҴ������ȣ�ʵ������ر��찲����ʱ³Ѹ�ո�30�꣬��Ϊһ�����˵��ͻ�֮�ꡣ�����ľ����ȣ����ݿ��£�ʱʱ������������������������ò���䡶��¥�ϡ����������Ļ������꣬���ڿ��Ƶ��������Ұ������ˡ�����д�����������ѵ�����˵�����ͻ�����������ַ����飬�����������֣��˷���ѧ���Դ����Ƹ�����Ҳ�����Գ��е����θ�֮�ԡ����пɼ��ӱܻ����Ľ�����³Ѹ�Դ�Ů�˵�̬�ȡ���Ů���紼�ƣ��ɽ���ų����֮��ȴ��֮������ͬһ������ɮ���е��Ŵ���������ľ��������ѡ����ȶࡱת�Ƶ�������ֽ�ѣ��������£�������ƻƾ������ɡ���С˵�����������찲���ܼ��긴һ����ؿշ��������صȴ��ֵȴ����������ഺһ���ή��û��һֱ������ݵƣ�������ϡ�
����1912�꣬³Ѹ�ܲ�Ԫ��֮�������Ͼ�ת��ƽ*��ְ��ǰ���꣬��ס�ڡ�S����ݵġ��������ݡ���ݡ��ź�����˵�������������һ��Ů�ˡ�����ҹ�����Ӷ��ˣ���ҡ���������ڻ����¡��������Ļ�����ÿÿ���������ͷ���ϡ����ɼ��������ȡ�³Ѹ�������ij�����DZ����ʷ�����ű�����Ƭ�����������£�һ�Ȳ���һ��ذ�ף�Ѱ˼��ȥ�Լ�������������1919��Ǯ��ͬ�����������������ں�Х������Ϊ�������ź�������д���������ռǡ���ƪ�¡���txtС˵�ϴ�����
³Ѹ���ĸ�Ů�ԣ�2��
1919��11�£�³Ѹ�������������ݵ�Ǯ�������˱����˵����һ������ʽ�ĺ�Ժ����Ϊ�ܼҳ��ӣ�³Ѹ�д��ͥ���롣����ĸ�����찲�ӵ���������������Ժ������������һ�ҡ������ܽ���һ�ң���ס�ڴ������ڶ�ͯ��Ϸ�ĺ�Ժ����ʱ��³Ѹ���찲ͽ�������Ļ����Ѿ�ά����13�ꡣ³Ѹ���40���찲����43�����������Ա���
����³Ѹ��������ص������찲���������˵����ʱ����׳���³ѸΪѹ��*���������˯Ӳ�崲��³Ѹ�Լ�Ҳ��������˵����һ������������ѹ�����������ϳ�̬�������仯����������仯�����ƫִ�����������ζ�����������
����1923�꣬³Ѹ�������˷�Ŀ��ϯ���߶����ߣ��ᵽש����ͬ�����֮ǰ��³Ѹ�����찲��ȥ�������ڰ˵��壬���ǻ�������ң��찲��Ȼ�ش𣺡��˵����Ҳ���ס���Ҷ����˸�������ֶ��ֶŮ������ʲô�����������Ҳ����ȥ����ᵽש����ͬ��������Ҫ�������շ����첹��ϴ�¡�ɨ�أ���Щ���ҿ���������������ʮ���Ա���ࡣ
����1924��5�£�³Ѹ��ծ���¹�������������ͬ21�ţ������ҵĺ�Ժ����������һ������������һ��Ҳ��������֮����������ͬ��һ�������£��ճ����棬��ͬİ·��������������Ի���Ҳ���ʲ�ζ�̵���Σ���Ӧ���ͷ����Ի���ǡ��롰���ǡ����찲Ϊ³Ѹ�����㣬³Ѹ��֮������������ĸ�����Ȱ˵������Ȼ��������³Ѹ֮��������Ȼ������һ������֮�㣡ĸ�������찲��ʲô���ã�³Ѹֻҡҡͷ�ش𣺺���̸������̸��ûζ������ʱ������������³Ѹ����һ�����ӣ���һ�Σ��Ҹ��������ձ���һ�ֵ��ĺܺóԣ���˵�ǵģ��ǵģ���Ҳ�Թ��ġ���ʵ���ֵ��IJ�������û�У�ȫ�й�Ҳû�У������ܳԵ���
����³Ѹ������ƽ���Ϻ����Ӻ���һ�����찲ͬס���᷼�����Ժ���ô�죿�찲������ʧ����˵������ȥ���������Ҳ��ã�����ú÷�������һ��˳�����������ܻ�õġ����ִ���һ���ȷ������Һñ���һֻ��ţ����ǽ��һ��һ������������������������һ�������ǽ���ġ�����������û�а취�ˣ���û���������ˡ��Ҵ����ٺã�Ҳ�����á�����˵�����������Ⱳ��ֻ�úú÷��������ĸ��һ�����ˣ���һ������������Ӵ�����һ���Ϊ�˿������Ժ���������ǻ�ܵġ���������ʱ���찲����һֻ��ţ��ص����ˡ�³Ѹ���˺�Ӥ���찲��¶ϲɫ��Ϊ�Լ�����֮�������е����ѡ������ţ��Լ������к�Ӥ������ֽ���������ͺ��£�����������Ϊ���ǹ»�Ұ���������µ��������������ܶ�����
����1944�꣬�Ə������Ϊ����³Ѹ���Ȱ�����³Ѹ���飬����ƽ��������³Ѹѧ����������ͬ��ȥ�ݷ��찲����ʱ���찲�����ǰ��Բԣ�����˪�ݣ�����ƶ�ࡣ�찲����ס��������˵������������˵³Ѹ���Ҫ���棬Ҫ���棡��Ҳ��³Ѹ�������Ҳ�ñ��汣����ѽ����
����������ΨһҲ������һ���ź�������ž�ε���Ѫ����������³Ѹ������������Ϊ³Ѹ���������������һ���ˣ�һ�����ӡ��غ����գ������˶���һ��ʱ��������Ʒ�����찲���ɳ����˼ӱ���������ʹ�ࡣ��һ��������ʹ�ֱ࣬������³Ѹ��³Ѹ����˵�Լ�Ҳ�ǡ�������һ��������������������������ƽ���ܺ�Ӥ�����찲����һ������Թ���ȵļ��ͣ�����һ���������ӵ��乬������һ����³Ѹ���������������ͬİ·����һ�������ھɻ���������Ů���У��찲���������š���������һ����
³Ѹ���ĸ�Ů�ԣ�3��
��������ʱ�ڣ�³Ѹд�����ź�������Ұ�ݡ�������ǻ���Ƿ�����ƣ�ϣ����������˼䣬��д����Ů�������Ϊ�������ﱬ�����ģ�������н�������̬ѹ����Ȼ����
��������³Ѹ����̫����
����ѧ������˵����³Ѹ�ĸ��������У��������¶����Ĵ���dz��صġ�һ�������Ļ������һ��������ܵ������˵�ʧ�͡��Ӱ˵���Ǩ����������ͬ����³Ѹ���ͥ��������𣬴Ӵˣ���������ྴ���������ˣ���Զ�ط����ˡ�
����³Ѹ�������ˣ�һֱ�ֵ����飬³Ѹ�Զ��ܵ��չ������ɣ��������еء������縸������ĸ��˵�������ֵ�ס��һ��ʮ���Ѱ���������ֹһ�ε����ҵ���˵���ֵ������ּҡ�������³Ѹ�������˵�ʧ��ԭ���������ء��������ϣ�ֱ�ӵ�������Ϊ����̫���ӡ�
����1923��7��19�գ������˸�³Ѹ����һ������ţ�
����³Ѹ������
�����������֪����������ȥ���²�����˵�ˡ��Ҳ��ǻ���ͽ��ȴ�Ҷ����ܵ��ܵ���Ҳ������˭������Ҷ��ǿ������˼䡭���Ժ��벻Ҫ�ٵ����Ժ��������û�б�Ļ���Ը�㰲�ģ����ء�
��������
��������ʮ���ա���
�����ֵ����˴˶�ʱ������ռǶ����ɲ��ꡣ�������º�˺ȥ��ҳ�ռǣ��Ը���ԭί��������˵��������⡣������Ҫ˵���ҵIJ������Ʊ�����˵�Է��Ĵ�����ȻҲ��Ҫ�ٳ�Щ���ص����������ϡ��ⶼ�Dz�����˵�úã����߲�����˵�ģ���ô��ʹ������Ч������˵����Щ������Ҳ����Ц������ǰ�����������Ž������𣿡�
���������������ڶ�ѧ������߷״���³Ѹ����̫֮��Ĺ������£��������Ǿ����˵����ࡣ
������̫���ӣ��ռ�Ů�ӣ�����³Ѹ����������ѧ�ձ���ס�����ᡱʱ����̫�����ǵ�ʹŮ����˵����Ů����ƶ��ȴ��ϲ�ݳޡ�1909�꣬������������飬1911�꣬Я�������֮�찲����̫���Ӽ������������м�����ɫ���־�˵������Ъ˹����֢������֢������ʱ��������߽��
������³Ѹ���������Ѻ������ܽ��˵Ļ����У��ֵ�ʧ�͵�ԭ�������Ϊ���ӳּһӻ����ֲ���³Ѹ�ġ��ҳ�����λ���������ϣ������ˣ���衱�����Ÿ��˲��ԡ�����³Ѹ��*��н��ÿ��300Ԫ�����н��Ρ���ѵ����룬������Ҳ��ꡱʸ������˵������һ��ְԱ�����룬�Ѹ߳�10�����������Ȼʱʱ�ݣ����¿��ա�³Ѹ�����Ͷ٣����������ǻư�����������������һ�ң����붯���γ���ū�ͳ�Ⱥ�������ݻ���³Ѹ����̾���Լ��ư��������ģ����еýγ����ߵģ�
����³Ѹ�Ӱ˵��������Ը������¡�ֱ��1936������ǰ����ĸ�������л���˵�����DZ��˵�������ģ������Ŀ������ĸ˵���������Ͷ������IJ��ͣ���ȫ���϶��Ĺ�����������û�п������ǡ�³Ѹ���Ƿߣ����۵�д���±���ʷС˵�����¡��У�����ʱ������Ϊ��֮��������˵�����硱���Ӽң����գ���Ů�����������ӳ����ӷš����DZ�������ձ�Ů�������ȥ�ġ�С˵�У����϶�̻���һ����Թ�ԡ���ѻը���桱�������̷���ҩ���µ�Ů�ӣ����ڷ�����λһζ̰ͼ���ֵĶ���ϱ���������뿴����
³Ѹ���ĸ�Ů�ԣ�4��
��̫������³Ѹ��ͥ������һ���������ᡣ³Ѹ������һ����ϻ�ӵ�������û�����������³Ѹ���ἱ���߳����ȵĴ��ͥ���룬�ܷ���������ƽ��������Ԥ������ˡ�
������������ʱ�ڣ���д�������±ࡷ���ຬɳ��Ӱ����������Կ������༤���븴�𡣡������±ࡷ�����������������ʱ�ֵ����䡣��
��������³Ѹ������ƽ
��������Ů��ʦ����ѧ��
��������ϵ��ʦ³Ѹ����ѧ������ƽ�ĵ�һӡ���ǣ����糤��ͷ�����ֶ���Ӳ����ͦ�����ţ����á�ŭ����ڡ������϶ಹ����ƤЬ����Ҳ���Dz������ڽ�̳���������£���ˣ���ϥ�ǵĴ���Ҳ�ڸDz�ס�ˡ�
���������꾴���ĵ�ʦ³Ѹ��������˼������˸�ŵ�����������â���������ϣ���Ȼ��������䣬�������������������й�С˵ʷ�Ŀ����ϣ�ѧ������ƽÿÿ���ڵ�һ�ţ�Ŀ�����������ң�д���������ݡ�
����1925��3�£�³Ѹ�յ���һ����������ţ�����������̡��й�Ů�ӽ�����ǰ;�������⣬��ĩ�����ǣ����̵ܽ�һ��Сѧ������ƽ��³Ѹ����ͻ����ţ�������ƽ��Ȼ���ѡ�������������ţ��������ˡ������顷��һ������Ҫλ�ã�Ҳ����³Ѹ������ƽ����ľ�������
�����˺����˵��������Ƶ�ݵ������в��ϵرŷ���
����ͨ��һ���º�����ƽ��һ�ε�³Ѹ�������ļ����͡�����³Ѹ����Ϊ���ϻ�β�͡����鷿�У�����ƽ��һ�֡�̽�ա���������С�
��������ƽ��³Ѹ�������ഺ�ķ硣��ɬ��������������â���еĻ�����ʱ��³Ѹ�������ش�����⣬��Ůѧ���Ľ���Ҳ�����ſ���1925�����ڣ�³Ѹ������ƽ�ȼ�λŮʦ��ѧ������ҡ��᷼�������ҳԷ���ϯ��ƺ���̸֮�ʣ�³Ѹ��ֹ��������������ȭ������ij����С������ȭ�ǡ����֡���С��������ƽ��֮ͷ����������֮���ã���������֫��֮���ɡ�³Ѹ�ƺ�Ҫӭ���������гٵ��Ĵ����ˡ�
����Ȼ����³Ѹ�����ϱϾ���������ʮ�������Ļҳ����������ص���������һҡ������ӭ���µİ��顣�����������������壺�����ԣ����ǰ��ģ�����һ�ң���Ϊ���Լ�������ȱ�㣬������û�˶��֡���³Ѹ������ƽ�������Լ������֡����⡱�롰���䡱��ĩ�����ʣ���Ϊʲô��Ҫ���أ�������ƽ��Ӣ��ʫ�˲�������ʫ��Ӧ�ԣ��ش���ޱ���ࣺ����δ�������룡��
������Ϊһ�����ѵ���ʵ��������һ�������Ĵ��������ߣ���֮�ڽ�������������ɳDZ���������³Ѹ��������һ���㽶����ǵ����Ѿ���������ȷ��������ϵ���ݿ�֤Ϊ1925��10��20�գ���ǰ���죬³Ѹ���������İ����˸�С˵�����š��������Լ���û�и����İ���Ļ����뷴˼��Ҳ�Ƕ�����ƽ��һ�ֻش𡣿������š������ǿ��������顱��ȴ�ǿ����˰�������³Ѹ�ġ���ա����Ӿ��İ��������Ƕ�ô�¸Ҽ�������������Լ��ģ�����˭Ҳû�и����ҵ�Ȩ������������İ���̬���������ڿ���ʽ�������ŷ�����Լ��İ��˷���˹���������������������ҡ��ӱܻ������������뾯�裬���������ޡ�
³Ѹ���ĸ�Ů�ԣ�5��
���ǣ����Ӿ������¸ҵ�����ƽ����³Ѹ�����˰���쮷硣
�����������˼����Į��ѹ�ȣ�һ��һ�����Ű��ķ��ۡ�
��������1925��10�£�����ƽ��ͬ���ߡ�����
����������Ҳ�գ����൱Ҳ�գ��Ϸ�Ҳ�գ����Ϸ�Ҳ�գ��ⶼ�����Dz���ɣ�
��������1925��10�£�����ƽ���������ҵİ�������
����������ij�������ϣ��ӽ����������������ͬ��������������ά��˹�ĵ�������ķ�������֦�ϵĻ��������������衣������ƽ������������Ҵ����£�³Ѹ���ڲ�����һ��ܾ��ڻ��ı���������ƽ�������ϻ�β�͡����鷿��������ס�������֣�³Ѹ����չ��һЦ��������ƽ˵������սʤ�ˣ���
����1926��8��26�գ�³Ѹ������ƽһͬ�˳����¡�³Ѹ��������֮�������Ŵ�ѧ�ν̣�����ƽ���Ȼع㶫�ϼҡ�
����1927��10�£�³Ѹ������ƽ���Ϻ�ͬ�ӡ���һ�꣬³Ѹ46�꣬����ƽ28�ꡣ�찲��³ĸ��Ȼס�ڱ����������ļң���³Ѹ���������öȡ�
�������˵Ľ�ϣ��ܵ����������۹�����
���������Ĵ��������Խ�ŵĶ��������ˣ������³Ѹ�˾��ǡ�һ����ò��Ȼ�ߵġ�*��˽������һ������Ϊ�����³Ѹ�����ꡱ����������˵����³Ѹ����������ijij����ͬϯ������������������̫̫��������֮������Ůѧ��������ϵ�������¹�ϵ����������˽�£����������в���������������֮������
�������ܣ�����ƽ������ͬ����Լ����������Ϊ��������dz��˵�����֮�⣬û���κη���������������˴˼�����Ͷ��ϣ���ͬ��һ������������ྴ���������Σ��Ͳ���Ҫ���κε����ס����Dz���һ�еľ���̶�Ҫ���������ԣ���ʹ�˴˼�ijһ���治���⣬������Ҫ������Ҳ�ò��ŷ��ɽ�������Լ�������ʼ��������ı���ģ��������û��ͬס��һ��ı�Ҫ����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