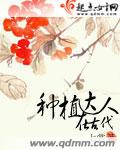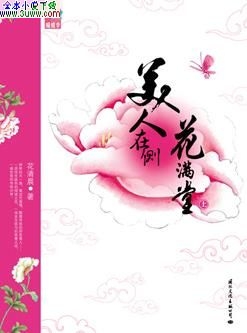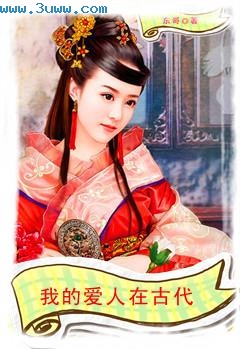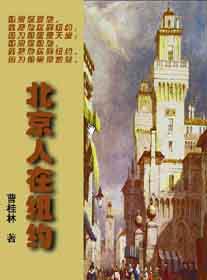人在胡同第几槐-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明灭;有的年轻恋人是观赏为次欢聚为主;或演出间进进出出,零食不断;或坐席上姿态做派不雅;有的年轻父母望子女成龙成凤,却又不会教育指点,台上音乐偶像献艺,台下幼龙雏凤比抖腿还要嬉皮。
愿以母亲留下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并供大家参考:要像爱惜每一篇字纸一样,珍惜这辈子亲眼看到的每一场演出。
。 想看书来
找不同
那天从城里书房绿叶居去往农村书房温榆斋。到了温榆斋门口才发现忘带开门钥匙,只好再返回城里。轮换在两处书房里活动,已有八年之久,忘带开门钥匙却是头一遭。难道我已成了一个“恍惚的人”?
《恍惚的人》是一本小说的书名,作者是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这本小说在“*”后期作为“内部参考读物”在中国翻译出版。当时译介它,是认为内容具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老人尴尬处境的进步意义。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出版社将其正式发行,被当时如饥似渴地扑向外国文学的读者们飞快购尽,于是加印几次,达到很大的一个印数。我那时读这部小说,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冷静的写实工力,有一个细节,写冬日老人来不及入厕失禁,在廊檐下往雪地里尿出一串“冒号”。说它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对老人的冷漠,当然是一种解读,但作者其实是透过老人题材,写人性,探讨生老病死这一永恒的主题。花无百日红,人有衰老时,未老者如何对待老者?老者如何面对自己?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课题。“恍惚的人”需要在夕阳箫鼓里有尊严地默默燃尽生命最后的光焰。
一九八一年,我参加三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赴日访问,在东京见到了《恍惚的人》的作者有吉佐和子,她是一个带男相的妇人,而且做派也很有点中国古代梁山好汉的气概,她和我们代表团长杜宣是老相识,知道杜宣在“*”中吃了苦头,见杜宣那天腕上无手表,当即抹下自己腕上的一块高档手表,让杜宣戴上。她说话直来直去,听说《恍惚的人》中译本印数已达十万册,我们本来以为她会高兴,没想到她板起脸问:“谁让你们印那么多的?”竟然生起气来。从那一天起,我算知道了他们那边的文化,和我们这边文化的一大不同,就是雅文化包括纯文学和俗文化,包括畅销书,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虽然二者也有交汇融合的部分,好比两个各有圆心的大圆边缘互割,形成一处暧昧的“叶子瓣”区域。但两个大圆那“叶子瓣”区域外的广大部分,是互不相干的。有吉佐和子是一个纯文学作家,她写的书拥有一个固定的读者群,出版她的书的机构绝不会亏本,她当然也能获得不菲的版税,过着尊严的小康生活,但她不是畅销书作家,一听说把她的书印得那么多,她本能地觉得不对头,认为是给她错定了位,有违她的美学追求。当然我们赶忙给她解释,中国人口那么多,十万册的印数其实并不算很多,当时重印了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一刷的册数就要多许多。这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日本文化方面大体是量的增加大于整体结构的变化,而我们这边的变化,可真大得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可以说是瞠目结舌,不仅是量在激增,结构性的改变与不断的转型,更惹人注目。
有吉佐和子和杜宣已经相继过世。他们都值得我忆念。跟他们接触不多,但觉得他们都是始终没有恍惚的人。所谓没有恍惚,指的既是生理上没有痴呆,更是心智上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
人到老年,生理上的病变导致恍惚,以至痴呆,有时候是无法抗拒的命运之诡。生理上的种种退化是可以通过积极预防和锻炼来减缓的,而心理上的疾患更是能够以清醒的自我定位来加以排除的。我对自己说,偶尔忘带钥匙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倘若经常地忘记自己的位置斤两,浮躁抑郁起来,那可真是自我催命了。
这两年,很偶然地到《百家讲坛》录制了关于《红楼梦》的系列节目,又连续出了四本相关的书,反响强烈,书也畅销,但我自己很清醒,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作家”需要本本书都畅销。我自己看重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和特殊文本的《树与林同在》《私人照相簿》这两年都重印了,数量都不大,引不起争论,吸引不了多少眼球,而且,我从一九八六年后半年起,编制也不在专业作家系列,我现在就是一个爱画风景写生画自娱的退休金领取者。“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每天《晚报》到手,必要翻到有找不同漫画的那一版,无论是有八处还是九处不同,我总能一一找全。我很快乐。在仔细看图的过程里,相同处令我想到人己相通,而不同处激励我保持个性。全与人同不是好的人生。有几处与众不同之处,才不枉在世一场。我也许还会再有忘带门钥匙的失误,但我不会有失却自我的迷茫。
谢幕与终曲
至今回想起母亲,在剧场演出结束后,那样重视演员谢幕的表现,还不禁感动。
她不仅会随着大家一起鼓掌,微笑地仰望着走到台沿谢幕的演员,还总是嘴里喃喃有词,发出些感叹赞扬,仿佛人家会听得见似的。她总属于把掌声坚持到最后,直到幕布合拢再不掀开,才意犹未竟地离场的那批铁杆戏迷之一。不等回到家中,在公共汽车上,她就会抿着嘴笑,跟家里人宣布:“今天谢幕六次啊。真精彩呀。”或者说:“别看今天谢幕才三回。其实也很了不起。”她很少有对演出不满意的时候,当然,那也是因为剧目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父亲只爱看京剧,母亲除了京剧,其他剧种比如评剧、曲剧、河北梆子也都喜欢,而且也很爱看话剧,我小时候跟母亲进剧场观剧的次数最多。
母亲重视演员谢幕,当然首先是对演员有一份浓酽的尊重。她说过嘛,应该像爱惜每一篇字纸那样,珍惜每一回观看到的演出。但那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理性支配下的礼貌。母亲有感悟艺术的天性。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跟她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孙维世导演的,金山主演。那出戏展现的生活和人物不仅离我那样一个中国少年极其遥远,其实与一直并没有走出过国门的母亲也很隔膜。但是幕布一拉开,记得第一幕布景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外省农庄花园一隅,穿西服的绅士和穿拖地长裙的淑女慢条斯理地在台上活动着,从树阴下的长餐桌上银闪闪的大茶炊里接茶喝,说着一些很平淡的话,我开始真有些“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不知不觉左腿抖动起来,母亲感觉到了,用右手轻按我左腿膝盖,轻声在我耳边说:“看他们多不顺心啊!”母亲这一句提示,竟让我一下子捕捉到了此剧的情调,我像母亲一样专注地观看,渐渐从那些似乎平淡的对话里,听出了味道,小小的心于是琢磨起来:景色那么美,穿的、吃的、住的那么好,可是这些人为什么那么不快活?……当然,整出戏演完,我也不能说真看懂了什么。演员谢幕的时候,母亲照例感动地久久鼓掌,我也跟着鼓掌。回家的有轨电车上,我跟母亲说:“这戏好。”母亲问:“好在哪里?”我就说:“万尼亚舅舅跟他侄女儿索尼娅说:你的头发真美。索尼娅说:一个人长得不美的时候,人们就会安慰她,你的头发美……”母亲微笑了,笑得像缓缓开放出一朵花,说:“能记住这么几句台词,也不枉你看了这么一出戏,他们也不枉演了这么一场啊。”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话太老了。其实还可以说些“年轻话”——戏吸引人恰是因为不尽如人生,而人生的诡谲其实远非任何戏剧可比。现在回想起母亲带我看戏的种种情景,忽然憬悟:观戏的最大意义和乐趣,是在人生中镶嵌进一些“美丽的停顿”。
母亲带我看了戏,也熏陶出了我的文明习惯。母亲仙去二十年了。现在我进剧场不多了。但一旦去剧场观剧,我总是提前进场,中途绝不“抽签”。我最见不得那些未到幕落就站起来撤退的看客,我总是以真诚的鼓掌和仰望来对待演员谢幕,离开剧场回家的途中,我会回味那些最打动我的片断。
西方古典歌剧正式开幕前,往往会有好几分钟的序曲。多数西方电影的最后,是一边放映详尽的演职员表字幕,一边响起终曲,有时终曲会是一首很长的歌,像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就不是穿插在情节流动当中,而是放在最后字幕走动时,由席琳?迪翁深情唱出。许多中国观众还不习惯在电影院里静坐到全部字幕走完,欣赏完终曲再离座,有的影院甚至也不待拷贝彻底走完便停止放映;一些人士在家里看光盘,就更不耐烦听电影的终曲了。记得三年前我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看一部法国电影,故事结束后黑底子的字幕走动了大概有五六分钟,但只有少数观众离场,多数人都静坐在座位上欣赏那伴随着字幕的终曲。我置身在异国他乡的那种情景中,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虔诚地对待演员谢幕,我更加铭心刻骨地意识到:沉浸于艺术,是我们人生之旅中“美丽的停顿”。
二勇
那是去年春节前,村友三儿跟我说,村里老秦家有一副二勇。我不信。那玩意儿能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世道沧桑,保留到如今?
所谓二勇,是一种布制傀儡。它上半截是两个摔跤手面对面扯臂的形象,茁茁实实的。下半截呢,没被耍弄时就是空空的一条肥裤子。半个世纪前,我还是个少年,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京,很快融入了新的民俗氛围,在东庙(隆福寺)和西庙(护国寺)的庙会里,都看到过民间艺人表演“二勇摔跤”。那表演的爷们自己穿一条跟傀儡的裤子一模一样的肥裆裤,彻底地弯下腰,把自己的两只胳臂套进傀儡的裤子,把头部隐藏起来,这样,那二勇就成为了两个揪扯在一起的摔跤壮汉。表演者变换种种技巧,自己的双腿和双臂巧妙地移动、磕绊乃至踢出躲闪,使观看者觉得就是有两位勇士在专心地搏斗。那傀儡的上半部虽然看上去就是假人,但是因为下半部的灵活运动,不断地颤抖摆动,也就以假乱真,让看客在真真假假的谐谑表演中获得极大的乐趣。表演完了,艺人从傀儡的裤子里褪出上半身来,一定是满头大汗,两条粗壮的胳臂青筋暴起。在他转着圈抱拳作揖的时候,会有一多半看客转身离去,但也一定会有一些看客往搁放在地上的傀儡身上扔钱。我那时也就把妈妈给我的零花钱,拿出二百扔下去——我说的是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二分钱。现在的年轻人会哑然失笑吧?你那么抠门!但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在庙会里吃一碗炸丸子——过油的素丸子用滚水煮了撒上些椒盐,撇一勺稀释的芝麻酱,再撒上点香菜叶——很香啊,二百块钱一碗。
其实,那种一人演出呈现两人景象的傀儡戏,也不都是“二勇摔跤”。我后来还看到过几种类似的表演,比如“猪八戒背媳妇”,再比如“瞎子背疯”。——那傀儡的上半截是一个瞎子背着一个“疯婆子”的造型,所谓“疯婆子”,并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妇人,而是“疯瘫”(其实更正确写法应该是“风瘫”)即高位截瘫的妇人,为了表示其下肢瘫痪,还特意制作出了一双别在丈夫腰后的萎缩得不成比例的坏腿。和“二勇摔跤”不同的是,“猪八戒背媳妇”和“瞎子背疯”的表演者虽然也入套藏脸,但底下不是四条腿,多半用自己的腿脚表演丈夫的腿脚,而以自己的双臂表演媳妇的双臂。“背疯”把“疯婆子”乱指挥、瞎丈夫步步错的“洋相”呈现得淋漓尽致,有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但我很不喜欢。这类民俗性质的表演,有精华,有糟粕,“瞎子背疯”拿残障人开涮,格调不健康。多年前,我写过《丑媒婆可以休矣》一文。现在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组织民俗表演,比如跑旱船,应该删除那男扮女妆、唇边点着大黑痣、举着长杆烟袋锅、模仿三寸金莲移动艰难、摇摆扭捏的丑媒婆一角。
话说三儿带我到了老秦家,他家房子虽然改建过,正房里有一间居然还保留着砖炕,北墙根还保留着一个大躺柜,莫非那大躺柜里存着二勇?老秦见我急切地询问,觉得好笑,那算啥稀奇玩意?早该扔了!带我到东厢房堆杂物那间屋,从旮旯里揪出一样陈旧得不行的东西来,正是傀儡二勇!那两位勇士的造型,是辫子盘在头上,呀!该是晚清的遗物吧?老秦告诉我,那是他祖爷爷留下的,他爷爷还玩过。为什么能一直留下来?因为在讲究阶级成分的时候,他家成分好,没人来他家翻查,他们也几次打算扔掉,但总没彻底清理堆房,也就一直保存了下来。老秦说你喜欢这没用的东西你尽管拿走。我想起城里的一位朋友专爱搜集民俗旧物,就决定哪天带他来拜访老秦,收购了去。
但是,后来我忙来忙去,没顾上张罗这事。今年秋天带着我那位朋友来到我乡村书房温榆斋所在的村子,也没麻烦三儿,直奔老秦家。唉,你猜怎么着?老秦不在家,他媳妇告诉我们,那二勇已经被她拆了,铺在狗窝里了,那狗可是拉布拉多名贵品种,繁殖好了会有人一千两千地拿钱来买!
我十分沮丧。倒是我那朋友频频劝解我。他说“二勇摔跤”挺有哲理内涵的。细想也真是,人生、社会,说是双方争斗,其实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要想跟人和谐,先得自己协调好自己。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备好麻秸待踩岁
那天老友马君来我乡村书房温榆斋,一落座就高谈阔论。马君是个民俗研究者,他有一个观点我颇赞同,就是不能把所有民俗都博物馆化,有些民俗,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保持下去,比如踩岁。他认为以往的内涵就十分丰富,现在还可以注入更多的意义,推陈出新,成为除夕的一大亮点。
五十七年前,随父母初到北京,我还赶上过踩岁。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大型四合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