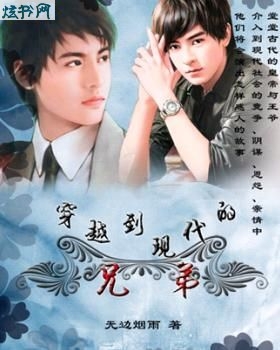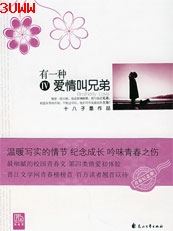汉城兄弟-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男人的军营故事和女人生孩子的故事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愿意把自己的
经历说得十分痛苦,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当然,一个是熬复员,一个是熬分娩。
一般男人都得有这个过程,一般女人也都得有那个过程,但先经历过的人总爱把
事情说得很严重,耸人听闻。今天这顿晚餐也没有例外,大家照例大吹特吹一番。
这中间少不了还要添油加醋,谈点往越南派滑雪部队啊,忠请北道的海军训练啊
等类的事。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纯属无稽之谈,越南地处热带,根本用不上滑
雪部队,忠请北道位于韩国内陆的中心地带,绝对无法进行海军训练。
升洲一口抿干了烧酒杯,说:“我认识的几个兔崽子中有到空军部队去的。
那几个家伙都是人死了还不倒架的种儿。老兵要给他们上‘行头’,上边就会有
人出来说话,让那些新兵脱光衣服上行头,这算什么事?!”
祖鞠接过了话茬:“我们专业有个小子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休假的机会,回
来歇些日子,没想到才几天上面就又来了紧急命令,好像马上要爆发战争似的让
他赶快回部队,心急火燎地赶回去一看,是连队之间要进行足球赛,缺个人,让
他去补缺,气得他直翻白眼。”
“那个小子的部队还有从南汉山城去的家伙呢,听说有一次他替连长的夫人
跑腿,把钱还丢了呢。可真逗。”
“嗨,我想起来了,我们同学在上课的时候,有的人老交头接耳,老师一说
他还顶嘴,被老师给打了个美。”
“记不清哪个主儿了,他只要一拿到考试题就犯晕,说印的题目看不清,哼
哼唧唧地老折腾。”
“对,我想起来了,有个小子作弊的办法可真绝,有一次他借口忘了系裤带,
从兜里掏出了裤带往腰里系,趁监考老师不注意就把塞在皮带扣儿里的答案掏了
出来。”
“不知你们听说了没有,有的小子还进了部队精神病医院呢,精神病医院哪,
多怕人啊,那是个完全封闭的病区。一听就知道,军营和精神病医院是连在一起
的。当然,不用说这要比把军营、精神病医院、监狱、修道院连在一起好一些喽。”
“咳,那算什么。用我哥的话说比这厉害的还有的是。家庭,家庭算个什么
玩意儿?我嫂子和祖先哥不也组成家庭了吗,前一阵儿,我嫂子不就让祖先哥给
裂了吗?”
听到这儿,我就半道插了一杠子,觉得应该说几句,让这几个小子明白“裂
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别让他们再胡拉乱扯地瞎诌了。我说:“哥们儿,‘裂了
’这个词并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它原本是一句部队用语。在部队,如果有人说
‘把他裂了’,那就是说狠狠揍一顿,打他个半死,直到骨头打折为止。这本来
是一个地形术语,是指硬石头上裂璺,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是指骨头上裂的璺。当
然,这个词在医院也可以用。有时出了交通事故,为什么要给受伤的人拍片呢,
就是要看看他骨头有没有裂璺,实际上,这个词用韩国语的意思去理解就是‘裂
出纹路’的意思。”
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用最通俗的语言把这个词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好让
这些无知的家伙增长点见识,可没料到这两个小子就像没听见似的,不理不睬。
我一直认为,自己在俱乐部中是个学识渊博的“秀才”,是把其他几个人凝聚在
一起的中心人物,但现在看来这个“中心”已经开始动摇了。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我自命清高,假模假式的那种“才子”劲头在一天
天降低。高中是我最为得意的时候,也是“才运亨通”的时节。有一两次,我还
把自己写的诗说成是歌德写的,故意拿给“当代才子”崔炳道看。
“嗯,真不错,歌德写的嘛,那还能差。”
我得到了崔炳道的称赞,心里美滋滋的,无形中我感到,自己已经赢得了
“当代才子”的尊敬和友情。
我自认为懂得多,学识渊博,所以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摆出一副哲学家、艺术
家的架势。崔炳道对我的内心世界是一清二楚的,却从来没有流露出一点点反感
的情绪来。可我则不然,当我看到他发表在文艺杂志上的那篇小说时,简直恶心
得想吐。这篇小说矫揉造作,充满了酸腐味和乳臭未干的稚气,内容除了自我陶
醉的低级趣味外,就是庸俗不堪的笑料。作为朋友,我对他的心思才智自然是了
如指掌。
祖鞠和升洲表面上常常对我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但在内心深处,他们还是
认为我肚子里是有点墨水的。尽管他们俩并不了解我的内心世界,是两个被卖掉
还帮人数钱的大笨蛋,但和老狐狸崔炳道相比,我觉得他们还是蛮可爱的。
现在时间还很富余,我就把升洲和祖鞠送到了公共汽车站。这里已经接近南
韩和北朝鲜的临时军事分界线,所以坐车的几乎都是些大兵,他们一上车就靠窗
口坐了个一字长蛇阵,都把旁边的座位空了出来。看来,这些当兵的即便互相认
识也不愿意坐在一起,他们把旁边的位子留着,都在暗想,说不定能碰上好运气,
哪个汽车站会上来一个妙龄少女和自己坐在一起呢。这样也能饱饱眼福嘛。
祖鞠在上公共汽车前,突然脑袋里闪出了一个念头:斗焕是不是已经参过军
了呢?
人都是有多副面孔的,一生中不出一次错的人可能在某一天成为连环杀人犯
;一个夸夸其谈,能说会道的人也许有一天会成为抑郁寡欢,沉默少言的“哑巴”。
听说,一个杀人如麻的黑社会老大竟为了救溺水儿童而被江水夺去了生命……总
之,谁都不会是一个永远模式化了的人,其行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偶然的时间
往往会变得十分反常,甚至判若两人。
祖鞠想当学徒工的想法也是突如其来的。男孩子们小时候往往爱玩电工活儿,
装个收音机啦什么的。而祖鞠呢,偏偏有些特别,说他是男孩儿嘛,并不太像,
他不喜欢玩电工活儿。可不是男孩儿又是什么呢?谁也回答不出。祖鞠对男人们
爱玩儿的活计——赌博、推牌九什么的一窍不通。和祖鞠打牌等于在和小狗一起
玩游戏。也许祖鞠知道自己脑子不够使,才把那一点点脑容量留着,将来做男子
汉应当做的活计时再使用。
小狗玩到高兴处会摇摇尾巴或者亲切地汪汪叫几声,一点藏不住自己的感情。
祖鞠也一样,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明明白白表现在那张四方脸上的,让他连肛门扩
约肌都不收缩就毫无顾忌地放出个响屁是容易的,但让他不管抓的牌是好是坏都
要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却是很困难的。
然而,要说祖鞠在任何方面都是透明的,那又错了。论起装洋蒜的高明程度,
恐怕没有人敢和祖鞠媲美。不知是哪一天,他突然抛弃了去工大上学的机会学什
么摄影。对这一举动,别人都不理解,他后来却洋洋自得地说:“我差点让自己
的艺术天才被埋没了。”可如果谁认为他将来要当摄影师,那又错了。祖鞠的抱
负不是这个,而是当一名记者,特别是随军记者。他要随着军队纵横疆场,把如
火如荼的战斗场面都记录下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崇拜拿破仑和挪威探险家南森,
想让这两个人的特点都能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祖鞠十分清楚,自己有两大“特
长”:一是能颠能跑;二是对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绝不姑息。说起这第二条来,没
有一个人不认为他的心是又黑又狠的。
祖鞠想当记者,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做梦而已——这一点,连他自己也十分清
楚。要真正成为一名记者,首先得有名牌大学的文凭;其次,录用考试得成绩优
秀。这两条祖鞠都不具备。
一般人从能阅读报纸起,都会从第一版往后翻。祖鞠则不然,他专拣时局政
治犯的判决栏目看,这个栏目里常出现的好多字他都不认识,每每把“不思悔改”
念成“不思每改”,把“怙恶不悛”念成“古恶不俊”,把“保镖”念成“保票”,
把“沉溺”念成“沉弱”,把“馄饨”念成“昆屯”,把“创口贴”念成“仓口
贴”,把“败北”理解成“北方败了”等等。就这个水平,不要说当记者,就是
去给记者提鞋也不够格。别看是位“白字先生”,他的心还蛮高呢,自己大字不
识几个,反倒爱拿起报纸挑记者的毛病,这个字写错了,那个字写白了,谁念得
不对。有人念“他特地买来啤酒”,他却硬说人家念错了,应该念成“他特的买
来啤酒”,因为动词前面的“地”应该念成“的”。弄得人家哭笑不得,不知说
什么好。
三月份,本来就要上学的祖鞠,顷刻之间希望又变成了泡影。要当学徒工的
事也泡了汤。所以,祖鞠又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就是当不成记者,当个
摄影师也好啊,人生免不了会有遗憾嘛。说也巧,在摄影班进修过的二哥祖织正
为了拍摄假面脸谱和护乡神偶像在全国各地到处转悠呢。看到无事可做,成天晃
荡来晃荡去的弟弟,就让他去给自己打下手。祖鞠时来运转,高兴得就像见了动
物园猴子翻跟头的孩子,又蹦又跳。他想:拍照那玩意儿还不容易,不就是手指
头一动的事嘛,不学都能会!
谁都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学摄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应该会
的祖鞠不学,却把时间尽花在运动会啊,集会啊,这样那样的活动上了。一有这
些事,他免不了要跟师傅跑前跑后,忙个不停。很快,两年就这样过去了。
别看摄影这个行当人数不多,但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学徒制度。
想当摄影师,首先得当摄影师傅的徒弟,在暗室里帮着师傅卷一卷底片啦,折叠
三角架啦,对一下光圈啦,师傅外出时帮他背背行李啦什么的。做好这些工作并
不是件容易事,首先得进行体能训练。背上一大堆摄影设备在烈日底下站几个小
时而不晕倒,这是徒弟必须会的一项基本功。另外,还得眼尖手快,会看脸色。
师傅把照相机放在一棵大树底下,就应该知道要照这棵树了,得赶紧把三角架支
好,把遮拦镜头的树枝打掉;师傅把照相机放在有冰凌吊子的屋檐底下,就知道
他要照冰凌吊子了,除支好三角架外,照完以后还得赶紧把那些冰凌吊子打掉,
以防别人再照。
一个高级摄影师所带出来的徒弟,必须是一个为了让照片达到预期效果,能
把影响画面的电线杆子拔掉,会爬到天上把多余的云彩抹去的主儿。徒弟是哪位
名师带出来的,决定着他将来能否在摄影界出人头地。没有本事不要紧,但一定
得投靠一位名师去闯荡世界。像祖鞠这样,一没本事,二又是刚刚从一个新创建
的学校勉勉强强毕业,没有任何社会背景,想在这个行当站住脚那是很困难的。
祖鞠只想成名成家,对世道却一无所知,对自己的使用价值更是没有掂量过。他
的本事和能耐在师傅的最后评语中,充其量只能用“要实现自己的愿望还得加倍
努力”这句话一笔带过。
祖鞠为此十分苦恼,也着实彷徨了一阵子。毕业后一年都没找到工作,游手
好闲,无所事事。后来,一个高班同学把他介绍给了一位野外摄影师,说:“这
个人物的德性和你比较般配。”
这个野外摄影师既是个现场摄影师,又是个探险家,他曾经孤身深入非洲的
原始森林深处,拍了几百卷胶卷。据祖鞠所说,那个摄影师赴现场实拍时从不先
做准备,而是随机应变,量体裁衣,在千辛万苦中求得摄影成功的乐趣。
听说这位摄影师在小学的时候就当过童子军,后来解甲从影,在摄影界,他
只能算个新手,一些同行对他的作品并不欣赏是很自然的事。
端着优质的照相机,随便摁摁快门,然后再从几千张的照片中筛选出一两张
好的作品,这就是摄影师的工作。干这种行业,时间搭进去多少不说,就是体力
也是够难支撑的。有人还会挖苦说,那个摄影师拍的照片,连狗熊都能拍出来。
更有人说,森林里的大象用脚踩一下相机的快门就能照出那种德性的照片。很多
人对这位摄影师的评价既简单又干脆:咳,哪谈得上什么摄影实力呀,纯粹是用
人工换来的瞎片子。祖鞠一听这话可高兴了,一拍大腿:行啊,他就是我学习的
榜样!我没有什么实力,他也没有。他能拍出这种照片,难道我就不能?!——
祖鞠终于替自己找出辩护的词儿来了,别人对自己怎么评价就无须去管了。最重
要的是,大象的脚都干得了的事现在却还由那位新手在干,那我这个英雄不就也
有用武之地了吗?他满心欢喜地琢磨着:这就像一出电视连续剧,刚刚拉开序幕,
片名权且叫做“英雄的胜利”吧!想到这儿,祖鞠霍地站起来,把自己的座右铭
——“人生有胜又有负,此时不搏待何时”大声背了一遍,就毫不犹豫地投身到
野外摄影师的门下了。可意外的是,这位摄影师的手下已经有两个人了,那祖鞠
的位子究竟应该怎么摆呢?这可叫祖鞠犯难了。升洲的工作也很不顺利。他嘴
上老喋喋不休地怨这怨那,但实际上过得比谁都舒服。
升洲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又聚在一块喝了一顿。那会儿我们并不知道后来升洲
换工作会换得那么勤,权当“开门大吉”,留个纪念吧,几个人就这样凑在一块
儿了。当时,祖鞠对升洲说:“你小子现在有工作了,这是贤珠姐姐出钱供你上
学所收获的成果啊。”
祖鞠的这句话并不是指贤珠姐为升洲出大学学费那件事,而是指高三的时候
贤珠姐花钱让他去补习学校“加餐”。那时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升洲却一点书都
没看,最着急的是升洲的妈妈和姐姐。姐姐说:你得下决心复习,千万腾出点时
间来好好看看书。可不管怎么说,升洲还是我行我素,该干什么干什么。没办法,
姐姐只好出钱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