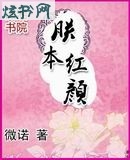梨园红颜-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童童,童童!”
童童“呀!”的一声惊醒过来,却是蝶儿坐在身边轻轻的唤她。
“你做梦啦?”蝶儿关心的问,“是做噩梦吧?……”
“是啊,梦见从高处摔下来……”
“谁都会做这种梦的,”蝶儿安慰道,“那是你又在长高呢。”
“原想躺着歇一会儿,就睡过去了。”
“可要小心些,这样穿着衣服睡着了,要着凉的。”
“没吵着别人吧?”
“没有,你看燕子睡得多甜,”蝶儿轻声的说,“要不今晚咱俩睡一床吧。”
“谢谢蝶儿……我已经不要紧了,你睡去吧。”
“真的?”蝶儿一边说一边回到自己的铺上,“那早点睡吧。”
“唉,晚安。”
蝶儿静静的睡去了,童童却辗转不能成眠。
窗外的风雨声时紧时疏,隐约像是又夹杂着阵阵的锣鼓京胡之声,顿时五颜六色的脸谱、彩旗在童童眼前飘舞,一条青色的水袖从彩旗中荡出来,又化作了一股淡淡的水气……然后是阵阵的喝采声。这一切都萦绕着童童儿时的梦。
童童的母亲淑贞是唱老旦的,扮上装,套上银发,那神态模样便和奶奶是一样一样的了。奶奶是母亲的老师,母亲就是从小跟着奶奶学演戏,学做人的。
冬天,场外下着雪,可一幕戏下来,母亲的额头上还是闪着细密的汗珠。奶奶便推了童童到母亲的怀里,又把泡好的茶递给母亲,这才开始指出母亲上一场的不足,母亲便会放下杯子,一字一句的跟着纠正。
童童听的多了,随口也能哼出腔调来,惹了打鼓佬在一旁啧啧称奇:“哎哟哟,没瞧出来,又是个角儿呀。”
童童最害怕母亲演沙奶奶,场上只要枪声一响,童童便哭得泪人儿似的,谁也劝不住,直等到母亲下了场,抱着童童说:“童童,妈不是好好的吗,那是演戏呢!”
演匪兵的大大跑过来,撅着屁股让童童踢。
奶奶便拧着大大的耳朵把他拽到一边:“小祖宗,她都闹成那样了,你还招惹她。”
大大呲着牙嚷道:“师娘,轻点,轻点,我这还不是让童童出气吗!”
童童瞧见了就又笑起来。
“瞧瞧,这一脸的眼泪鼻涕哟……” 奶奶也笑了。
童童的父亲童逢春学的是武生,扮相、做功、唱功都好,被人唤做“小连楼”。童童记得他拿手的戏有《挑花车》、《长板坡》。父亲和爷爷一样,扎了靠尚能从两层的桌子上翻旋子小翻下来,扎了马,纹丝不动。《长板坡》赵云有句白口“主公且免愁怅保重要紧”。每当童逢春念到此处,必获得满场彩声。一句念白能在全场观众中获得如此的剧场效果,实为罕见。爷爷只一提到小连楼,便是红光满面:“这小子,我的徒弟!”
后来团里只排样板戏,不再让演老版戏了。爷爷和奶奶也离开了剧团,在城外桥头的小屋住着。老人家想不通,演了一辈子的玩艺到头来怎会是祸害革命群众的精神毒瘤。那些日子,爷爷喝酒特别厉害,又拮据,每次只能买乡人自酿的烧刀子。喝那酒伤身子,奶奶劝不住,总是一个人默默的流泪。
每到周末,小连楼便会领着一家子带着酒菜到城外老师的家来。爷爷总不高兴小连楼来,来一回难过一回,何苦来的。只是每次见着童童,老人的脸上才有了些微的笑容。
“我这什么都好,你师父的身子骨还硬郎着呢。”
“硬郎就好,只是这酒要节制些才好。” 小连楼劝道。
“戏不让唱了,再不好上两口酒,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师父心里清楚,用不着你来教训。只是往后这里要少来,对淑贞和童童都不好。”
“没事,团里都是师兄弟们照应着呢,有谁说闲话呢……”
奶奶和母亲总有说不完的话。说到爷爷的身子,奶奶的眼总是红红的。
“别看他整天喳喳呼呼的,他的事我最清楚了,近来比起往年是大不如了。”
爷爷便不耐烦道:“娘儿家,知道些什么!”
天黑了,小连楼一家又要赶回团里。奶奶便拿着手电把他们一直送到桥头,
“老师,您回吧,桥上风大 ……”
“你走你们的,我这给你们照着路呢,天黑看不清呀。”
等大家走远了,奶奶又追上来嘱咐:“往后我们这少来,记住啦?”
母亲的眼也湿润起来,
“老师,您就别操心我们了,您自己也要多保重,家里还有老爷子呢。”
奶奶还要送,夫妇俩定是不让了,她才站住。
走了很远,童童回头看是时,见奶奶还站着给他们照路呢。那手电发着黄晕的光,在夜幕里闪耀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回 梦境(二)
终于,那一段苦闷的日子过去了。
夏日的一天,团里余书记委派小连楼为代表,请已被*的爷爷再度出山,当时能讲老戏的艺人已经不多了。但爷爷正在住院,烈酒已经严重摧残了老人的身体。小连楼只是表达了团里的意思,依着奶奶和母亲的意思,还是推掉的好,静静地先把老爷子身子骨养结实,其他的都是后话了。
淑贞出去取药的时候,被隔壁病房一个苍老的声音唤住了。
淑贞进去一看,原来是团里的琴师杨老。他也在住院,就在爷爷的隔壁病房。杨老的女公子礼貌地给母亲让坐,杨老却一把拉住淑贞的手,先问了爷爷的病情,随后就老泪纵横,只是一个劲地说:“我没脸见他呀!”
杨老是团里的饱学之士,他几乎给当时剧团的每一位名角都操过琴,以其长期的艺术熏染和高度的鉴赏水准,在改革戏曲之处,他便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和建议。然而同爷爷一样,正是这些建议让杨老饱受屈辱。淑贞记得杨老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只是爱收集几把古琴。“破四旧”时,一些学员冲入杨老家中,把杨老收藏的五把古琴一一砸成竹片子,杨老心疼得当场就晕倒了。
在爷爷的批斗会上,杨老却被第一个安排来发言。当时杨老有病,只说了一句话:“周连楼是顽固的保守分子,他假借维护文化遗产为名,死抱着封建思想不放,是极其反动的。”然后就被扶下台去,有了杨老的表态,其他人的攻击立刻潮水般的涌来。不久,杨老自己也被打倒了,偌大的年纪还得每天扛着扫把打扫街道。等爷爷离开剧团后,两人就再没有见过面了。
淑贞回病房偷偷同奶奶说了,爷爷瞧见便问:“什么事,偷偷摸摸的?”
奶奶说:“杨老就在隔壁病房,刚刚还拖淑贞问你好呢。”
爷爷腾的坐起身来:“走走,我要看望杨老去,我们已经多年未见了。”
两位老人见面后,大有劫后余生的感慨。爷爷从来没有提过批斗会的事,这让杨老感激了一辈子。
爷爷提到团里请他出山的事,杨老却极为赞同。爷爷本是个闲不住的人,出院后就径直往团里去了。
市里第一场传统戏是在政协礼堂上演的,一批刚*的老领导点名要看的却是爷爷的《走麦城》。
天特别的热,红绒的幕布在灯光照射下,把礼堂映得火一样通红的颜色。
童童帮爷爷点燃三只香,供在了窗台。
爷爷在脸上抹了粉底,然后上了红彩,勾脸的时候,手却抖起来。
“童童,过来给爷爷勾个脸。”
于是淑贞便把着女儿的手,细心的勾起来。淑贞似乎自幼就有着绘画的天赋,什么样的脸谱,她只看上一眼就能勾出神采来。这点一直是为童童所羡慕的,如今的童童对脸谱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也不能不说是母亲自幼就给了她极好的艺术熏陶。
“童童,你说爷爷老了吗?”
“爷爷不老,爷爷还能演大英雄呢!上台比谁都精神……”
场上锣鼓喧天,爷爷重上舞台,一招一式神采不减当年,丝毫看不出他是已上了年纪的老人。台下彩声不断,多年来,礼堂头一次这样的火爆。
奶奶却有些坐不住了,这些年,老头子功夫有些放下了,又好喝酒,这样演下去可吃不消的。
一幕戏下来,爷爷累得浑身都是汗,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淑贞给爷爷端来一杯水,爷爷接下却没有喝,童童看见他脸颊上全是汗水。锣声响起,爷爷起身就要上场,头一晕,幸亏淑贞在身边扶住。小连楼想着换下师父,却让他给骂了回来。
“你撩开幕角看看,这一排排的都是白发的老人了,好意思这样偷奸耍滑?”
爷爷拄着大刀深深地吐了口气,眼里霎时又有了光彩,他一撩战袍,重新又登上了舞台,大刀一耍,舞出片片刀光,场下一片的喝采。
奶奶却拉着童童来到窗前,爷爷供的三支香还缓缓的冒着青烟,奶奶双手合在胸前,默默的祷告着。
童童只感到热,那锣鼓声一阵响似一阵,到处是红旗翻滚,把场里场外映得通红,闷得透不过气来,空气中回响着爷爷那已略显沙哑的嗓音:
罢了哇!罢了!
想当年立马横刀风云眼底,
杀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夷。
今日里困麦城身临绝地,
一着错反受这群丑相欺。
兄王!大哥!
失荆州负重托岂能无愧?
纵有这擎天手难以挽回。
关羽乎!
大错铸成倥偬后悔?
雄心壮志岂化灰,
卷土重来会有期。
台上的关羽已被东吴的兵士团团围困,一会是黄脸的周泰,一会是黑脸的韩章,走马灯似的围着转,他东拼西杀再也杀不出重围,最后那赤兔战马一嘶长鸣倒在山谷,老英雄喷出一口鲜血,翻身倒下,便再也没有起来了。
奶奶也晕倒在后台……
爷爷逝去的时候没有谢妆,脸上还留着童童给勾的红净脸。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爷爷逝去不久,淑贞也病倒了。弥留之际,她拉着童童的手:“童童,妈要是不在了,你怕不怕?”
“童童不怕,您不是好好的吗,这是演戏呢!”童童把脸贴在母亲的手上。
“你妈一生都在演戏呢,”母亲苍白的脸上浮出一丝的笑意,“想歇歇了……”
淑贞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童童能念上大学,嘱咐丈夫一定要让童童上学,别像自己一辈子只能在戏里体会人生。
自从淑贞逝去以后,小连楼变得寡言少语,爱一个人独自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着屡屡的白烟从口里喷出,升到头顶时就散开,淡淡的变成天青的颜色,互相缠绕着消失了去。
一天,童童路过新华书店,听到一段老旦的唱腔,那声调和母亲唱的竟没有什么分别,童童听过久久不忍离去。几天后,她终于买下了这盘磁带。到家,童童迫不及待的拿出录音机,才听了开场的过门,却听见里屋“咣”的一声,父亲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童童,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书不好好念,还听这个?”
小连楼还从来没对童童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你哪来的钱?啊?”
童童已经吓得话都不敢说。
“怎么不说话了?唱戏有什么出息?”小连楼脸刷白的,他把磁带扔在地上,一脚踏碎了。
“不要踩……”
童童尖叫着扑过去。
“童童!你也学会顶嘴了……”
小连楼拿起录音机狠狠砸在桌角上,童童听见机器粉碎的声音。
“那是妈妈买给我的!”童童嗓子沙哑着,一头撞在父亲的腰上,自己却瘫倒在了地上。
小连楼慢慢的转过身,坐在了床沿上。童童看见父亲居然哭了,这铁一样的汉子,眼角闪出了晶莹的泪珠……
童童头一次觉得父亲苍老了,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已经长出灰白的头发了?
八月的暑期,倔强的童童瞒着父亲报考了戏剧学校。她是自幼练功的,考学不是难事,加上她长辈们在文化界的威望,学校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好苗。
童童拿着通知书独自跑到母亲的墓前。那是一个无风的下午,整个陵园就只有童童一个人,太阳照着一块块的石碑,发着惨淡的白光。童童抱着母亲的墓碑放声痛哭,又有谁能知道这瘦弱的姑娘心里承受了多少委屈与悲伤……
空旷的陵园里,仿佛又回响起母亲的唱腔:
有几个孝子听娘来论,
一桩桩一件件娘记在心。
那大贤舜耕田为的都是孝顺,
丁蓝刻木、莱子斑衣、孟宗哭竹、杨香打虎,
俱都是那贤教的儿孙,
我那不孝的儿呀!
这几辈贤孝子休得来论,
还有那不孝人说与儿听:
青风亭张继保他天雷报应,
韩信将未央宫速报幽冥。
为娘言语儿不肯相信,
怕的是我的儿头上有四值功曹察看儿的身。
我的儿行孝道将娘奉敬,
自有那天爷在暗地里查巡。
“妈妈……”童童猛的从睡梦中惊醒,窗外依旧是漆黑的,风雨声似乎要穿透过厚厚的玻璃,重重的压到童童那娇小的胸膛上来……
第五回 香楠烟雨
周日的清晨还绵绵的飘着雨线。
童童轻轻掀开窗帘看看,玻璃窗上沾满水珠,滴滴划落,留下道道泪痕。对面老屋青瓦上业已枯黄的瓦楞草重新又挺直了腰杆,迎着风雨瑟瑟地抖着。经过一夜雨水的冲刷,这些陈年的瓦片开始闪闪发光,乌亮的,就象古代武士镔铁铠甲上的鳞片。
“雨还没停呢 。”
童童的心底升起一丝的懒意。
蝶儿推门进来:“还没起呢,大小姐?我帮你买了早点。”
“唉,起床真是件痛苦的事啊!”
蝶儿便笑起来,
“好好的一个周末,又让这雨给冲泡汤了。”
“哎,说着了!这就是正经八百的——泡汤……”
蝶儿正喝茶,乐得一口水全都喷将出来。
童童拧开台灯,坐在床上看书,随手把书签放在桌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