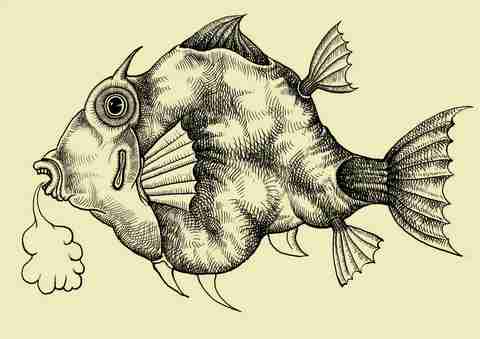深夜急召(1)这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真实,以至于我几乎不敢相信它曾经发生过。每个情节都似乎不像毫无准备,倒像是早有预谋。我的记忆似乎在搞恶作剧,交织着痛苦与快乐,五味杂陈。这才构成了酸甜苦辣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才会成为永恒。 随着船桨的一起一落,轻舟划过平静的湖面,穿过垂在湖面的柳条和树荫的倒影。我站在晃晃悠悠的小船上,她则静静地坐着,用灵巧的手指拨开那些零星的小枝条或挡住那些弹回的柳条,以免自己被划伤。湖水在柳条的映衬下呈现出金棕色,绿荫覆盖的河岸就像块祖母绿宝石。我们坐在阴凉处,周围的嘈杂和令人昏昏欲睡的嗡嗡声交织在一起,这世间的诸多烦恼和喜悦,全然抛在了脑后。在那乐而忘忧的独处时光中,这位年轻女孩抛开了一贯的端庄,梦呓般向我诉说她孤独的新生活,低沉悲伤的声音让我感受到了在那所大房子里,她跟她父亲以及每一个亲属之间有多么疏离。那段时间里我们彼此无须信赖,无须同情,...
--------------------------------------------------------------------------------新医学对于神经衰弱的病症,有转地疗养的治法。我在和霍桑初期合作的那一年,经过了一次实验,认为确很有效。就在那时,我的人生经验上又刻下了一条惊险的深痕,我的日记中也因此增加了一页新颖的资料。某年,我因着笔务过分繁忙,神经上起了些异症,症象是健忘,感觉过敏。我们的老友何乃时医士便竭力劝我转地疗养。我依了他的话,霍桑就与我一同到南京去休息。我们在江口中华旅馆中住了不满三个星期,我的精神果然就慢慢地恢复。我自然非常欢喜。六月二十九日那天,天气还不算十二分热,华民表常在九十七八度之间。我一清早起来,穿了一件短袖汗衫,系了一条短裤,赤足拖着拖鞋,身体上感到非常舒爽。我吃过了早餐,躺在一张藤椅子上,口里衔着一支纸烟,向窗外闲瞧。江口外滚滚的浊浪反映着金黄色的太阳,一闪一闪地发光。暖风一阵阵吹着。穿...
《生死两分钟》图书内容两分钟能决定人的一生。问任何一个曾经走错路、违反法律的人有关此两分钟规则,他们都会告诉你,两分钟,正是你从抢劫到警察到来之前所期望的时间。打破此项规则,可能会终其一生在监狱。虽然如此,仍有在会不按游戏规则行事…… 霍尔曼是一个职业罪犯,至少在那次抢劫银行时违反两分钟规则之前他是。当他在银行待到第四分钟时,被赶来的FBI凯瑟琳?波兰逮捕了。豪曼从此以后被关押在监狱;而波兰则辞职回家专心抚育孩子。然而不久她的丈夫却为了另一个女人(他的秘书)而离开了她。 当霍尔曼终于获得假释出狱时,等待他的并非是晴朗的天空。他脑海中唯一的想法就是与其感情并不亲密的儿子瑞奇(讽刺的是,儿子是一个警察)和解,重享天伦之乐。然而,听到的却是令他伤心欲绝的消息:他的儿子和另外三个警察在他被释放前天夜晚洛杉矶的一次血搏中被枪杀了。负责调查此事的警官安慰着霍尔曼,并告诉他凶...
神秘来信(1)夕阳如血,沙漠层染,红波千倾。 捉摸不定的风,如一个顽皮的小姑娘,瞬间奔跑在沙丘间,尘土飞扬;瞬间在地上打滚,卷起沙柱,“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瞬间捉起迷藏,悄悄穿梭在如红色竹笋的雅丹林;累了,静静坐在地上,倾听钥匙旋转的声音,“嘀咯嘀咯”,还有我的心跳——“叮咚叮咚”响。盗楼兰古墓,是我第一次,不知机关如何?古墓石块砌的,墓门铜锈斑斑,幸好锁是黄金铸的,不但没锈,还很灵敏。 钥匙在金锁孔里逆时针旋转5圈,旋不动了。我欲抽出,钥匙却卡在锁孔。我用力一拨,突然听到“轰”一声巨响,古墓往下沉。我顿时失去重心,如一块石头掉下墓井去。黄沙从井面流下来,洒在我脸上,粘着汗珠,如镀了一层沙膜,嘴巴、耳朵、眼睛都是沙子。借着越来越暗淡的日光,我看到井壁是石块砌的。突然,钥匙被石壁撞飞,碰在石壁“丁当,丁当”作响。...
“奈奈,你最近都忙着干什么呢啊?天天捧着手机盯着看,要不是知道你不爱玩游戏,我都以为你是在玩游戏了。”同事甲好奇的问道。 “现在谁不是天天捧着手机低着头走路啊,奈奈这样也是正常现象啊,不过,我说你小子这么关注奈奈,不会是喜欢上奈奈了吧?”同事乙起哄道,其他同事也跟着哄笑了起来。大家也都是善意的取笑,要是奈奈那个不开窍的听到这些取笑可以开窍的话就好了。奈奈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不折不扣的迟钝孩子啊。 最先开口问的同事甲脸红脖子粗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虽然他的确是有点喜欢奈奈吧,不过奈奈平时太安静了,简直就是三好女青年的典范,按时下班,按时下班,下班就回家,绝壁是新时代绝无仅有的好女人啊。不过,也就因为这,奈奈被归为可远观的冷漠女神了。但是他就是没办法想靠近一点,再试着靠近一点,说不定奈奈什么时候就开窍,知道他喜欢她,然后,他就可以抱着美人归了啊,渐渐地,同事甲陷入了...
江南春早 作者:冰糖梓四月的天还透着冬天的凉意,应该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今年的春迟迟没有来——花木的枝干依旧光秃秃的,像是在埋怨春节那场百年难遇的大雪。初春午后的阳光是最好的催眠剂。王盟懒懒地趴在柜台后面,半启双眼对着水泥地上格子窗的影子发呆。太阳如果再斜一点,地上的明暗会勾勒出清晰的雕栏图案,如同木工雕凿它们时所绘的图纸那般。叮当——雕花木门的门角擦过黄铜铃铛片发出悦耳的声响。王盟从柜台里抬起头。来者一行三人。带头的是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的模样。一件毛色油亮的袍子从她的下颚垂到了脚面。女人的身后是两个二十来岁的男子,一个稻草头,围巾在他的脖子上绕了几圈,双手插在呢子大衣的口袋里,神情随意地注视着王盟。另一个男子,格子衬衫敞着领子,衬衫外面披着一件休闲西装。...
一九四三年,十月,江城。 因为宵禁与灯火管制的原因,偌大个城市空空荡荡,寂寥无声,陷入了一片死气沉沉的黑暗中,活象一个巨大的墓穴。 在城市一隅,青砖高墙中,窗户被厚重的深黑色布质窗帘牢牢地挡住,只在窗帘的缝隙露出了微弱的烛光,和影影绰绰的人影。 窗帘的另一头,是一间卧室,一个年约五十的瘦高男人站在大床边,像一尊雕塑一般呆立,目光凝滞。床上盖着一床轻薄的棉被,是一个闭着眼睛的年轻女子,模样清秀,嘴角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却一动不动。 蜡烛微微摇曳,在瘦高男人的身后,还站着一个身着素色长衫的男子,肩上挎着一只牛皮药箱,正唯唯诺诺地说道:“周老爷,我已经尽力了,小姐实在是病入膏肓,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了,也请老爷节哀顺变。”...
1 相遇之时耀葵一直认为,黑桃其实已经死了。 15岁时,在一次学校的年级活动中,耀葵认识了他。 那是一个貌似有彩虹的傍晚。 斜阳徐徐驾临,雨水刚刚冲洗过校园,天空却被调成粉红和粉兰交错的复杂色调,篮球场上被耀得地上反光一片。预定今日的篮球比赛并没有得到任何延期的通知,整个初三年级的同学们陆续鱼贯而来,湿漉漉的球场被一种诡秘的粉色所笼罩,所有路过此处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抬头仰望天空。 耀葵也在其中,她在两天前剪了个奇怪的发型,从正面看去,是蓬蓬短短的蘑菇云,后面的肩上,却飘着稀稀拉拉的长发。对于这样的发型,她完全失去了美丑的判断标准,她只是暗自为自己的独特所得意。她和几个女孩子同来,却并不想与她们交谈,目光向球场中的男生望去。几个穿着黄色篮球服的男生球场那边说笑,其中有个男生个子很高,她想看清楚他的脸,便不自觉地将一只脚架在了篮球架的底座上,她的视野渐渐被抬高,...